罗宏:1978,给我的塑像!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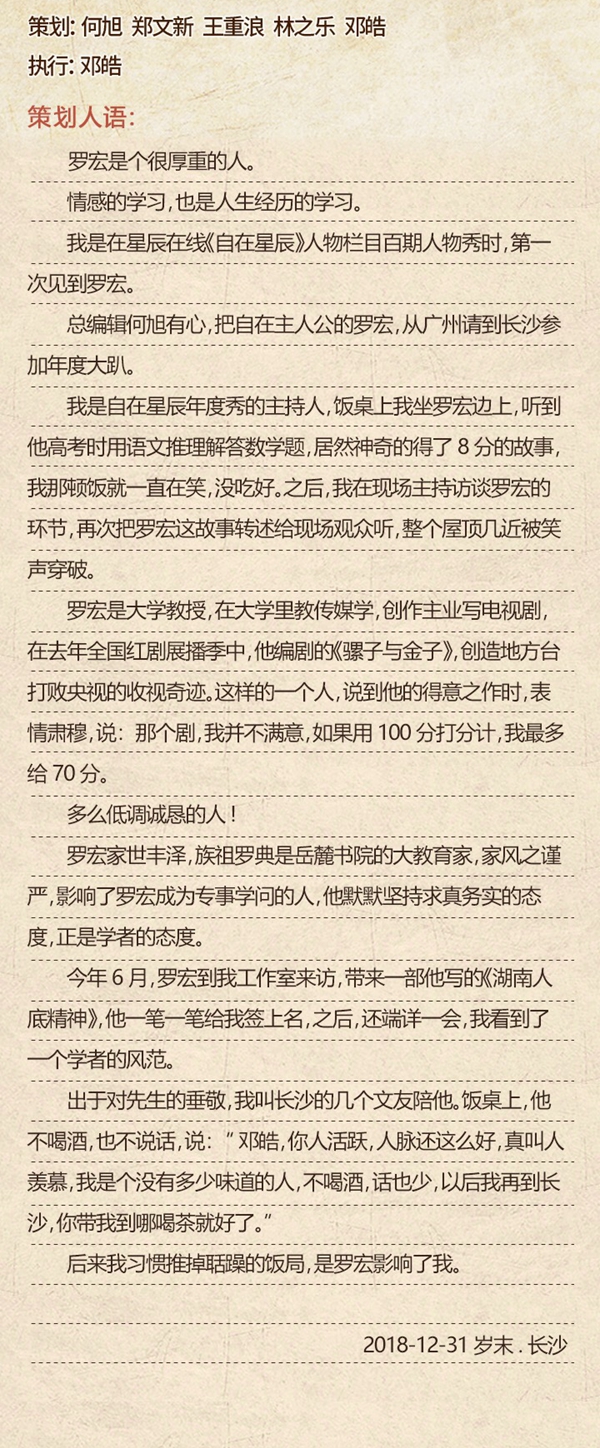

罗宏的1978:改革开放每一小步其实都曲折艰难
文/罗宏

(1978年,上大学之前的青年罗宏。)
报名
1977年秋冬之交,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到湘西边城小县,报名条件喜悦宽松,十年里各届毕业高中生或具有同等学历水平的青年,无论家庭出身,皆可报名。
我当时在一家街道工厂当电工,23岁。镇上管报名的文教干事是熟人,似笑非笑地看着来报名的我,“你是高中毕业么?我怎么觉得你是小学生,还只读了五年级。”我立即露出孔乙己模样的笑:“我有初中文凭。”该同志还是似笑非笑,“你的初中文凭怎么来的我清楚,就算初中毕业,也想考大学吗?”我傻了。
因为时代原因,我小学五年级就失学了。等到我父亲被平反时,正值知青大下乡,我14岁,连初中毕业的知青资格也无。组织考虑到在审查我父亲期间,曾耽误了孩子接受正常教育的事实,便安排我去了一所乡下公社中学插班学农,砍柴,插秧、编箩筐,参加文艺宣传队给农民传播理论思想……文化课基本上没有……就这样三个学期后,我拿到了初中毕业文凭。
于是我在知识青年下乡期间被分到一家基层街道工厂,当过木匠、铁匠、泥水匠,电镀工、采购员,最稳定的岗位是电工,从15岁到23岁,一干8年。后来我在小说中形容自己:“既不像高尔基也不像贾宝玉,倒是有点像顾城。”不知广阔天地有否历练出我的红心,反正练出了一心想去剧团当美工的我。私心向往剧团美工是公家人,可吃国家粮。8年来,我业余时间都在美术涂鸦,泡在美工梦里。我那时就这点志向。高考恢复之际,我野心开始膨胀,心想要是考上美院,没准就能和陈丹青做同学,再努力些,没准能当列宾,做个达·芬奇也凑合。
没想到报名遇质疑被揭老底,我好尴尬,但还是硬着头皮弱弱地问:“不是说同等学历也行吗?”该同志就笑了:“凭什么证明你有同等学历?我是高中毕业,你和我说说,什么叫函数?”我自然是不知道何谓函数的,但灵机一动说:“我考美术,不懂函数没关系,我知道印象派。”说罢,就跟他聊起了莫奈。他一直瞪着眼睛听,听完说了句:“好,我让你报名。”

(罗宏的人物素描作品。)
备考
报完名回单位迎面碰见女厂长,她劈头就问:“你报上名了?”我点头说,“报上了,人家说,有政策,单位应该给我一些复习时间。”女厂长立即沉下脸,“那革命和生产怎么办?”为了我的美工梦,我曾多次设法调离小厂,这位女厂长不同意,说我是人才,舍不得,使我一直不得梦圆。她寻常也认为我表现不好。于是我和她冷战多年,但在这个关键节骨眼,我知道厂长在敲打我,我连忙解释,我好歹也算得上是业务骨干之一。女厂长也怕我去镇上告状,便谨慎圆场说,“那你考虑下如何做到革命、生产和考试三不误。”
在经历一番破折后,接下来,我在有限的半个月里参加了高考复习班,主要是补习数学。第一次知道了数学王国里不仅有小数,还有负数以及函数等等。其实急功近利地补习并没有实效,我听得一头雾水,似懂非懂,但是老师穿插的数学小掌故令我如醉如痴。我感到,数学家是这个世界上顶级的智者,数学是个充满神奇和神圣的世界,我为之敬畏。时至今日,依然固执地认为,数学是人类最高境界的思维方式,缺乏数学素养,在学问上是无法登顶的,中国学人缺乏世界级大师,重要原因就是缺乏数学思维。数学也是我终身的短板,自感在学界里讨生活,也就是个混混而已。
半月的复习除了令我建立了对数学的终身敬畏之外,实际成效几乎是零,这在后来的高考中得到印证。此期间我还接待了一些省城长沙来的画家,如姜坤和李自建,我找来曼妙的苗女和苍桑的老农供他们画意写生。那时李自建也准备报考美院,他还鼓励我说,争取在美院同学。我明知自己的水平比他差了不止一个档次,心里却想,虽然我水平不如你,但在湘西考区,还真的舍我其谁。
回想这些往事,颇有感慨,那时候,真是不知天高地厚,如李贺诗云:少年心事当挐云。但也正是这份轻狂,支撑着我的青春自强。


(罗宏40年前的画意写生作品。)
高考
1977年11月某日,我参加了高考。看着考场操坪上密密麻麻的人头攒动,有同伴腿软了:天啊,这么多人,能考上吗?我顿时想起了拉斯蒂涅(巴尔扎克的小说《高老头》人物)面对巴黎灯火说的那句话:巴黎,现在我们俩来拼一下吧!
考试是闭卷,共四科:语文、政治、数学、史地。连考两天,第一天是语文和政治,感觉很顺利。因为每道题仿佛都可以有着自以为是的答案。我回答得较轻松,并没有抓耳挠腮。实际上,那届阅卷也不像后来,有着说一不二的标准答案,只要阅卷老师觉得有见地,还是能酌情给分的。第一天考完后我没有纠结,觉得尽力了,要是别人考得比我好,只有认赌服输。
第二天是先考史地还是先考数学,记不清了。我感觉史地也不算太难,失学期间我饱读大字报,其中有文史哲知识功底的好文章也不少,再加上平常我看过一些春秋、战国、西汉故事,三国演义、星火燎原之类的读本,中华史就贯通了,没觉得有多难。我工作期间还当过采购员,几乎走遍全国,地理知识虽比不上徐霞客,但和当时的高中水平也差不太多。
把我难住的是数学。对于只学过四则运算的我,简直像看天书。所有题目对我而言好像都不太陌生,又不知如何下手,但心想毕竟要考大学绝不能交白卷。正心慌意乱时,监考老师走过来,敲敲桌子:“莫慌,大家都不怎么样。先挑容易的做。”我顿时定下心来。只依稀记得有道15分值的甲乙丙组如何植树的应用题,我完全不懂列方程式求解,于是理了理思绪,写下了因为如何,所以如何,既然如何,推理必如何,成了一篇短文,终于凭借逻辑推理,把题目变成了加减乘除的运算关系。我答完后,考试时间快结束了,抬头一看,考场里没几个人了,不知离开者是完成了考试还是放弃了考试,反正我坚守走完了最后一公里。考上大学一年后,一位管学生档案的老师告诉我,我的数学得了8分。我想应该是那道应用题,答案对了,没有列算式,所以酌情给了我8分。
文化考试后,我又进入美术专业考试,考了四门,素描、色彩、创作,还有一门好像是速写。考场中,其他考生的画我都看到了,自信应该名列前茅,还因为监考的老师总是在我背后停留很久。走出考场后,湖南师范学院(现湖南师范大学)来湘西招生的周老师还问了我一句:你报师院了吗?我回答说,我的志愿是任何一家美院都可以,坚决服从分配。
对于上大学,我不挑食,因为没有本钱挑食。我只有小学文化底子,上任何大学都是祖坟冒青烟。况且我急于改变命运,憧憬像沈从文那样,走出边城,走出湘西,青春期的我,有着法国诗人兰波的信念——生活在别处。所以我不仅志愿报考了美术系,还同时报考了中文系,总之是东方不亮西方亮。考上大学,改变命运,这是最硬的道理。生活经验告诉我,理想不是用来憧憬而是用来实现的,要实现理想,就得骑驴找马,一步一步地来,任性是要吃苦头的。

(毛泽东诗词《沁园春·长沙》有云“忆往昔峥嵘岁月稠。恰同学少年,风华正茂;书生意气,挥斥方遒”。图为改革开放之初,罗宏与伙伴们的合影。青春正洋溢在他们年轻的脸上。<集体照最后排即罗宏>)
还记得考试完毕的那天或次日,一帮朋友聚在一起,大家都参加了考试,各自谈了感受,好像感觉都不差。这些朋友都是高中学历,平常都勤奋读书。我心里有些嘀咕了,这可叫我如何是好。同时明白考试就是竞争,逻辑公平又残酷——优胜劣汰,能者才能脱颖而出。这晚我很久才入睡,慢慢想开了,既然一样的试卷,我数学“瘸腿”缺乏竞争力,说明并不优秀,竞争力不够,在中文系录取上遭淘汰就得认命。但美术考生的文化成绩大都不行,我肯定会有明显优势,说明我还有戏。
继续去上班,女厂长关切地问:“考得怎样?听讲这次考试十年积压的高中生都来考,你只怕有点悬吧?我看你还是安心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为好。”女厂长是土改干部,文化层次不高,嘴巴却很能讲,消息也灵通,在街道干部中,也算是个麻利角色。我苦笑敷衍着说,我也只是碰碰运气。

(少年罗宏爱好“涂鸦”作画时的留影。)
录取
大约一个月后,阅卷结束,各种消息陆续传出,中心思想是说,到底是十年积压的英才大会考,各路才子才女倾巢出动,称霸考场,成绩超出预期的好,中华民族实现四个现代化大有希望。
我沉不住气了。因为我母亲是资深老教师,许多阅卷招生的老师都是她的同事或学生,探听考试成绩还不难,我便找到一位参加过批阅语文试卷的老师打探。此人其实是我小学同学,我当工人8年期间,他当了语文老师。他说:“是呀,这次考试成绩虽然一大批考生成绩并不理想,弃考的交白卷的考生并不少,但和招生录取的人数指标比,考生成绩还是超出预期的好,你要有思想准备啊。”我心就凉了,却不甘心地问:“你说说,语文成绩到底好到一个什么水平?”他迟疑了一下,有些神秘地拿出一份手抄的作文塞给我,“这是我们地区最高分的考生作文,你在这里看看,别到外面说呀!”我迫不及待地接过作文,没看两行就乐了:“这就是我的作文嘛!”他一听愣了:“真是你写的?”我立即滔滔不绝地背起来。他听完猛地给了我一拳:“厉害了,你有戏啦!”
我的作文立即就传抄开来,据说后来传至西南四省份,成为几届考生的备考范文之一,不言而喻,这意味我被录取只是领通知书的问题。等待期间,湖南师院来招生的周老师,邀请我陪他去写生,写生时对我说:“你等好消息吧。”于是,冬夜的睡梦中频频出现策马或者扬帆奔向远方的场景,还是慢镜头。可见那时的我多轻狂。朋友们都来祝贺,祝贺之余亦担心自己的录取胜算,我便不无虚伪地开导说,“我都能考上,何况你们?”大家就说:“你别哄我们,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痛。”当时我太年轻太轻狂,不懂人情事故。当然现在想来,高考后的忐忑不安是特别正常的心态。
没多久,周老师突然来厂里找我,把我拉到僻静处严肃地问:“你是不是得罪了领导呀?”我问怎么回事儿,他犹豫了一阵子说,“工作单位对你的表现鉴定很不理想,说你名利思想严重。要是这样,我们无法录取。”我顿时傻眼了,半天无语,很自然地联想起了单位女厂长一句话,“罗宏,我晓得你嫌我们厂塘小,想飞,你莫想!”厂长对我的态度,反映了当时一部分人工作的守旧思想。
周老师同情地看着我,又开口,“我几次找你们领导修改鉴定,他们不答应。我尽力了。不过你千万别闹,你还报了中文系,招生名额比美术生多得多,你又是地区语文‘状元’,还有机会录取。你要是一闹,就彻底完了。”说罢,周老师便离去了,我呆呆地看着他的背影渐渐消失若有所思。我知道,这个背影里夹杂着一名为人师者在大环境背景下虽爱惜人才、勉励年轻人但于个体而言又无可奈何的怅惋之情。周老师的背影连同他的名字,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
艺术生的录取完毕,北大清华等名校的通知书就来了,接着又是省城高校的录取书下来,我的朋友们一个又一个拿着通知书来报喜,个个笑逐颜开地说,“宏哥,还是你说得准,我们果然考上了”。说罢也不忘安慰我一句,“你可能是数学瘸了腿,总分受到影响,但肯定能考上”。我强颜欢笑,以示豁达,心里却丝丝苦涩。吹点牛皮说,我在朋友圈里不算领袖人物也算核心人物,现在却感到被边缘化了,如何想得开?
就这样一直熬到中专的通知书也下来了。第二批体检的考生都拿到录取通知书了,我这个第一批体检的语文“状元”还在等待。后来听说,我的语文上了90分,政治、史地也上了80分,总平均上了60分,是上重点的成绩。第二批体检的考生,平均分约40分。你说,我是不是比窦娥还冤?
要凭义愤,我肯定要大闹一场。但是心里死死记住周老师的话,没去闹,即使看见女厂长,也若无其事。倒是女厂长沉不住气了,故作惊讶地问:“怎么回事?你这个‘状元’还没有通知?是不是有人反映了你的表现呀?”我心里不快,脸上却是灿烂的笑:“没事,我听从安排!”
在录取的最后期限,湘西本地院校吉首大学招生组成员收到了我的高考成绩档案。在这所始建于1958年的院校里,有些老师是我母亲曾经的同事或学生,对我比较了解且同情。据说力荐录取我的是一位外语系的青年教师,也是母亲的学生。他告诉我:“我们看了鉴定,也作了研究,我发言说,罗宏我了解,这个年轻人是有些吊儿郎当,惹出过不少事,还被批斗过。但也坏不到哪里去,语文成绩又是‘状元’,不录取太可惜了。”这个叫刘小南的老师,我也终身记住了。
1978年初的一个下午,冬日阳光温暖而明亮,家门口的峒河水悠悠流向远方山谷。我望着河水发愣,眼神里透着绝望。徒弟四猛气喘吁吁地跑来,手里拿着一封信,话语急切:“师傅,你的信,是吉首大学来的,可能是录取通知书!”我打开信,果然被中文系录取了,眼泪慢慢流下面颊。
这年春暖花开的季节,我改变命运进入大学,开始了人生新篇章,祖国也一同走进了春天的故事。



(罗宏的美术作品。)
尾声
通过那场改变一代中国青年命运的高考,我有惊无险地登上了滚滚向前的时代列车,还有不少人被遗留在站台上。我的一个同伴学友就是其一。他也是第一批参加体检的考生,却因父亲的问题还在观察,于是政审没过关,未被录取。犹记得他来大学校园找我,两人坐在校园外的河坎上,望着对岸一片嫩黄的油菜田,他流着泪说:“我们的朋友都远走高飞了,只留下我一只孤雁。好在你没走太远,还能找你聊天。”我也流着泪了说:“我相信时代在发展,国家也会继续往前走,你父亲的问题会得到公正解决,你接着考,今年下半年我在校园等你。”
1978年下半年,他终于考进了吉首大学,成为我的同学。还有一批77级录取时不是因为成绩而是因为政策落选的考生,都在这届高考中被录取。所以78级是新中国历史上平均年龄最大的一届考生。如今77级和78级考生在各个工作岗位上起中流砥柱作用,我们这代人自强不息地证明了自己的存在价值。
往事如烟,改革开放不知不觉走过了40年。许多人关注到中国旧貌新颜的神奇巨变,我的故事则在提供另一种启悟:千万不要忘记,改革开放每前行一小步,都充满曲折和艰难。(文字整理/罗建勋)

(63岁的罗宏,头发花白,但看起来还很精神。 图片均为作者本人提供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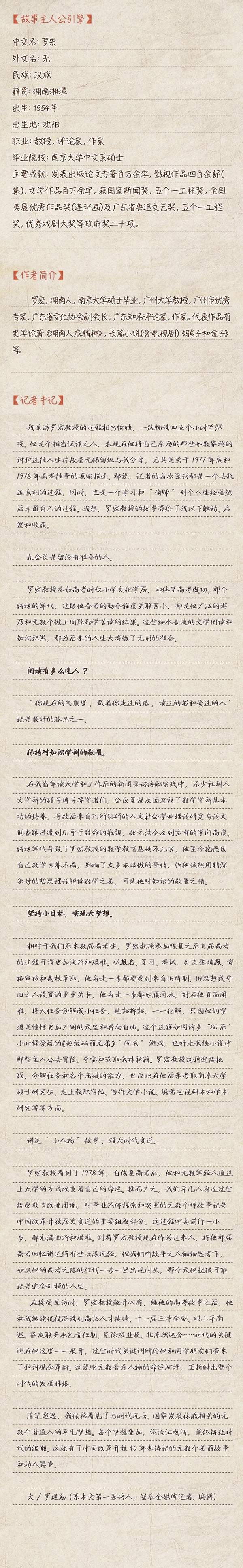
【来源:星辰在线】


